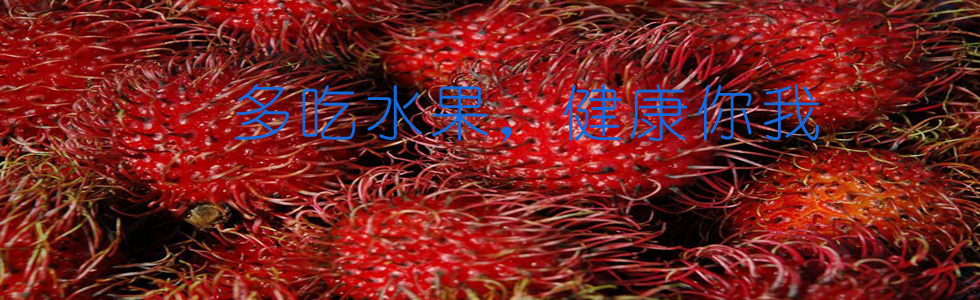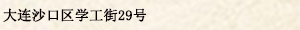秘密
窗隙呜呜咽咽吹着风笛,玻璃上映出两盏信号灯,一亮一灭地朝丹萍眨着。她把脸贴在纱窗上,一只暗黄蝴蝶在网眼下抖着翅膀,正趴在两灯下方,拼成个怪模怪样的小丑,鼻翼翕动着。
“看啥,”背后桌边坐着葛太太,扭头望向女儿,手里两根毛线针自顾自翻飞着打架,“还不写作业,都几点了?”
丹萍恋恋地把脸收回来,先前被她遮住的玻璃上,又得意地吐出一只火黄的舌头。
“早叫你写你不听,非捱到开学,现在忙脚丫子了吧!”葛太太往蜡烛前凑凑,指甲一节节扣着毛线结,嘴里数着,“啧”一声,又把多打的拆下来。拆着,又说,“你看这烟熏火燎的,怎么写?不得成个近视眼?等架上个镜子,有你后悔的,以后考大学,军校都报不了。”
“写不完,崔老师会打,”丹萍叹气。
“那还不赶紧写?”葛太太瞪她一眼。
“你不说会近视吗?”
葛太太停下手里的活计,“写不写?”
丹萍迅速溜到桌前。蜡烛扑扑地喘着,火苗牵着缕细黑绸子,《三年级暑假园地》正翻到“趣味数学”一页,饶有兴致地问道:
“小红说,我用36元买了4盒橡皮,每盒有3块。
小芳说,我用32元买了2盒橡皮,每盒有4块。
谁买的橡皮贵?”
丹萍吐吐舌头,三十六块钱!这么多的橡皮。那么,要用完多少铅笔?又要写多少字?三十六块钱呢。
“崔老师打你唻?”葛太太突然问。
丹萍回过神,写下个“小”字。
“嗯?”葛太太问。
丹萍抬眼,见葛太太仍打毛线,照常微攒着眉毛,不像个审问的神色。
“没有,”丹萍直摇头。
葛太太“哦”一声,扯了扯毛线,线球滴溜溜打了几个转。
丹萍“唰”地掀过一页纸。
过了一会儿,葛太太又问:“怎么打的?”
“扭耳朵,还踢屁股。”
葛太太手上一停。
“她打别人……”丹萍又说。
葛太太把活计一搁,按着桌子站起来,膀大腰圆的身子带些风,险些扑灭蜡烛。她拉开纱窗,用力掩了掩窗户,风声小下去。蛾子得到解放,习惯性地绕着顶灯飞几圈,发现停电,讪讪地落在墙上。
“过来试试,”葛太太回身拿起未完工的小毛衣,袖子还没接。
“又是我的?”丹萍扁着嘴。
“这可是马海毛,”葛太太卷起下摆对准丹萍的脑袋,往里套。
“什么毛东西……”声音毛毛地从衣服里传出来。
“你说什么?”
领口织小了,一路从额头抹到下巴,终于圈在丹萍的脖子上,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角也一道耷拉下来。
“你敢学脏话,看我告不告诉崔老师?”葛太太盯紧她。
“我哪说脏话!”
葛太太扯着丹萍的肩比来比去。
“我不想穿这种毛衣了,”鼻子里带着哭腔。
“别毛病,”
“吴美琳都穿买的!”
“人家考满分,你唻?”
葛太太扳着丹萍转个身,上下瞧瞧,领口匝得太紧,肩膀又嫌太宽,“啧”一声,念叨起来,“不缺你吃,不缺你穿,还不好好学!她爸就个士官,你爸爸可是干部,你怎么考不过……”
丹萍背对着她,突然哼哼唧唧哭起来。
“哭!”葛太太把她趔趄着转过来,“你还有理了?”
丹萍还是呜呜地哭。
“要哭出去哭,别在这乌殃人!”葛太太往门外推她,“你爸不在家,看谁管你!”
丹萍忙扒住桌沿,大红彩点的毛衣茸茸地箍在她上半身,像只受惊的小兽,喉咙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。
“就是你爸惯得你!他都几天没个信儿来,”葛太太哽了哽,“你还找事!不能让妈省省心?都多大了,妈能跟你一辈子?”
丹萍听见说,睁眼瞅瞅葛太太,绒毛的小胸脯一起一伏。
葛太太只作没看见,把头扭过一边,窗外乌压压的夜上映出一张妇人脸,宽鼻阔口细长眼,紧皱着眉毛,自来卷的头发束成个脑后圆髻,额前一圈细碎地扎煞起来。烛光摇曳里,外头海上的信号灯倏忽不定,不知是不是浪太大。
“妈,热,”丹萍嗫嚅道。
葛太太叹口气,转过来给她脱毛衣。丹萍举着手,眼巴巴地打量她,睫毛濡得湿湿的。葛太太捧住丹萍的脸,大拇指给她揩了揩泪,小圆脸不知在哪蹭的灰,哭得沟壑纵横,一擦更成个小花猫。
见葛太太脸上浮出点笑模样,丹萍缠上去:“妈,饿了。”
“饿了吧!叫你吃些七七八八的,饭也不正经吃,当心长不高!”葛太太嗔道,“吃西红柿炝锅面条吗?还打个鸡蛋?”说着起身去厨房了。一会儿听见丁丁当当地切西红柿,煤气灶“滋——扑”地点起来。
丹萍吸着鼻子,脸上紧巴巴的,《暑假园地》还剩五页没做,全是数学。鼻子又酸了。黄蝴蝶凑过来,迷迷离离地绕着她飞。又数了一遍,还是五页。蜡烛烧得直点头,脚下油汪汪的一滩。来不及了。崔老师明天坐在讲桌上,食指蘸蘸下嘴唇,一页一页地翻过去,到最后,抬起头来,怎么没写完?
葛太太端着碗进来,手擀面团坐在红稠的汤里,袅袅吐着白气。
“吃小鱼还是虾米?”她搁下碗,又转到厨房问道。
“妈,不想写……”丹萍苦着脸。
“现在上哪找蟹子?”
丹萍张了张嘴,只听厨房“哐隆”一声鼔响,不锈钢盘子打锣一样跳在地上,转着圈儿叫得欢快。
丹萍兜着嗓子,“妈?”
“妈!”她跑过去,葛太太仰面倒在地下,纹丝不动,墨蓝布裙直掀到腿根,露着白花花的肉,通红的虾米、银白的鱼干,洒落一地。
丹萍顶着风打开房门,楼道里黑漆漆,对门家偏偏没人。她又摸着黑往楼下走,背后有门响,一回头,还是黑。她听见自己发抖,脚跟蹭着一阶一阶的楼梯,没个完。
“开门!”终于喊出声来。
“谁?”楼下吴太太在门里惊疑不定。
“我妈死了!”说完大哭。
门打开,吴太太的手电找到丹萍的脸,背后躲着的吴美琳跳出来,“就是葛丹萍嘛!”
“怎么了?!”吴太太半蹲下,一只掌心烫烫地贴上丹萍的胳膊。
丹萍抓着她的衣角,叽哩呜噜说不明白,哭得倒清楚。
“别怕!带阿姨去看看,”吴太太说着,转身到厨房放下菜刀,“美琳,你在家等着。”
“这么黑!”美琳跳起脚来。
丹萍一嗓子喊破,“我妈要死了!”
“走,走!”吴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噔噔跑上来。丹萍一拉自家门,傻了眼,被风刮上了。吴太太也拽了拽,果然。
“葛嫂子?”她侧着耳朵敲门。
“妈妈!”
风呼呼的,余音散后,没别的动静。
“完了,你妈妈死定了!”美琳睁大眼,凑到丹萍脸上。
“乱讲!”吴太太嗔她。
丹萍呆了呆,“哇”一声嚎出来,躺到地上。吴太太好说歹说,连抱带扯,把她弄到楼下,嘱咐美琳:“你陪着丹萍,我去打电话。别让她乱跑!”
“我也去!”
“听话!”
美琳噘着嘴,“那你不许锁。”
吴太太带上门,钥匙在外头转了几转,锁了。
丹萍只是哭。美琳站在一旁举着手电,照照丹萍,照照屋顶。“葛丹萍,你别哭了!”
丹萍不理,半仰在黑皮革沙发上,哭得蹬脚。
“你把沙发都弄脏了!”手电光移到丹萍的脚,赤着,拖鞋早不知道踢哪去了。
美琳叹口气,坐到丹萍身边,缓声道,“你也顺便节哀,这样你妈在天堂里才能死不瞑目。”
丹萍也不睁眼,一脚踢到沙发前的小茶几,继续哭。桌上一只军绿搪瓷杯子,跟着茶几打个趔趄,泼出半杯水,顺着油革桌布滑到水泥地上,断线的珠子般。
美琳气得目瞪口呆,扯过条抹布堵在桌上,“你就气我吧!气死你妈,又来气我。”说着背过身去。
丹萍哭累了,渐渐止住,眼皮肿得老高,目光茫茫然从中挤出来。这时外头淅淅哗哗地嘈杂起来,分不清风声还是雨声。
美琳走到阳台处往外张张,又跑回来,抱着手电筒紧挨丹萍坐下,“外面真黑。”
丹萍呆着,一哽一哽地。
美琳伸出根大拇指,推着手电开关,屋里一道光柱——亮、暗、灭,灭、暗、亮——突然惊道,“路上没灯,我妈也摔死咋办?!”
丹萍闻声,缓缓扭过头来,“那我们都没有妈妈了!”她哑着嗓子宣布。
“还不是因为你?”美琳叫起来,跳下沙发,冲到门口,房门却打不开。“妈妈!”她隔着门喊了几声。
楼道里只有呜呜地回答。她后退几步,迟疑了一下,飞快地跑回来。
“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,”美琳挨着丹萍坐定,红着眼圈道,“妈妈一定死了。”接着捂住脸,嘤嘤哭起来。
“你别哭!”丹萍慌了神。
“你赔我妈妈!”
“我妈都没了,拿什么赔你?”
“谁稀罕你妈,我要我妈妈!”
“人死不能复生,看开点。”丹萍作为过来人。
“你妈才死了!”美琳伏到一边啜泣,腿边的手电滚在沙发上,摇摇摆摆地要往地下走。丹萍截住它,想了想,拿起来把光抵在下巴上,“吴美琳,你看!”
美琳扭过头来,见一张惨白的脸龇牙咧嘴,红舌头伸着,吓得“哇”一声叫出来。丹萍“嘿嘿”一笑。
美琳一骨碌坐起来,“你敢吓我,我把转笔器的事告诉你妈!”
丹萍心里一紧,脸上还挂着笑,“什么转笔器?”
“崔老师从你书包搜出转笔器!”
“我拿错了,”
“那么大个东西?”美琳冷笑。
丹萍涨着脸。她放在书包里三天,背着上学、放学,碰都没碰过。都没来得及碰一下!
“现在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,”丹萍试探道。“你当我姐姐吧。”
美琳端坐着,想了想,“那你姓吴吗?”
“我姓吴。”丹萍毅然道。
“你不要你爸了?”
“不要了,”他在军舰上,很久都见不到一次。
“那,你从现在起听我的?”
丹萍忙不迭点头。
“你坐着,我拿个好东西给你看。”美琳走到里间去,窸窸窣窣地翻东西。
丹萍扭了扭身子,硬革沙发皮发出吱吱扭扭的响声。
“不要乱动!”美琳的声音传来,跟着人也追过来,举着手电打量了一圈自家客厅,没什么异样,方才坐下,递过个东西给丹萍,“喏。”
一个滑溜溜的塑料壳子,蓝粉色的小汽车形状,带着个尾巴,丹萍摇着那车尾巴转了几圈,呆呆地问:“这是什么?”
“转笔器呀!”美琳嗤笑。
丹萍用手掌托着那转笔器,四个小车轮仔细地碾着她手心,出了汗后微微打滑,她声音瑟瑟地,“送给我吗?”
“想得美!”美琳一把夺去,“你可别打它的主意!”
“没有妈妈了,姐姐也不疼我,”丹萍嘴角一撇,“妈妈!”她哭喊。
丹萍——遥遥有个回应。
“妈妈?”丹萍睁开眼,细听。
“管谁叫妈妈?”
“嘘,我听见我妈叫我了。”
“你吓唬谁?”美琳气鼓鼓地,却忍不住抓住丹萍的胳膊。
丹萍循着声,扒开美琳的手,往门处走。
“葛丹萍,你……”
“听,”丹萍轻声打断。二人把耳朵贴在门上。
“什么也没有!”美琳敞开嗓门,颤着声。
这时门锁突然啪地响了,门身一动,两个孩子往后一退,齐声尖叫。
“怎么了?”门后吴太太慌忙拔下钥匙,探进身来。
“妈妈!”美琳一个箭步飞上去,挂在吴太太腿上,“我好担心你,没有你我可活不下去了。”
“这傻孩子,”吴太太摸摸美琳的头,“丹萍,你妈把门开了,快上去看看。”
家里黑咕隆咚,丹萍好容易才找到葛太太,歪在床上,一手抚着腰。
“你这孩子!”葛太太艰难地撑起头来,“妈妈摔倒了,也不知道扶,一眨眼跑没影了,碰上坏人怎么办?黑灯瞎火的,爸爸也不在家,谁教你大晚上跑出门的?”
“妈妈,你没死!”
葛太太啐了一口,“赶紧‘呸呸呸’,把那个字收回去!”
丹萍忙“呸呸呸!”表示自己说错了——天上那个爷爷耳朵真奇怪,平常千求万告他总听不见,但凡这些字眼儿蹦出来,他又有求必应了。
“这么大会子你跑哪去了?我在这喊破嗓子,你也不理?”葛太太问。
“孩子跑出来找人,你可别埋怨人家,”吴太太这时领着美琳进来,带着一圈手电光,“把孩子都给吓坏了。”
“阿姨,我都吓坏了,”美琳说。
“是吗,”光照着葛太太的脸柔下来,转头问丹萍,“害怕了吗?”
丹萍不吭声,葛太太吃力地伸出手,握握丹萍冰凉的脸蛋。丹萍又要哭。
“又哭!”葛太太手一甩,“今天怎么回事?”
“阿姨,她在我们家一直哭,”美琳说。
“就是,孩子害怕了,”吴太太把丹萍揽过来,“我都吓得要命,跑去打电话,小卖部还没开,亏你没事,要不我要撬锁了!”
“这时候,打电话叫谁?”葛太太笑道,“他们在舰上,还不知道漂到哪了……”
“家里还有蜡烛吗?”吴太太岔开话。
“最后一根,”葛太太努努嘴,桌上只剩燃后的一圈蜡油,“知道这会子说停电就停电,叫她赶紧写,不听!晚上又点灯熬油,弄得家里蜡都没有,”说着要瞪丹萍一眼,但躺着视域所限,只瞪到吴太太脸上,于是又把头撑起来,准确地再瞪一眼。
“没事,”吴太太把手电筒开到最亮,倒竖在桌上,“我们在这陪陪你们。”
“不用不用,”葛太太直摆手,“孩子明儿还上学。”
“明天我还要收作业!”美琳说。
“还早,待一会,”吴太太道。“你怎么样?”
葛太太想起自己有伤在身,虚弱下来,“我这腰给闪了,半天爬不起来,脚好像也崴了下子。”
“拿个热水袋敷敷腰吧,”
“在里屋柜子里,”葛太太对丹萍说。
“我去找,”美琳说着,跑出去。丹萍就没动。
吴太太低头查看葛太太的脚踝。葛太太背着她对丹萍使个眼色,丹萍问,“怎么了?”
葛太太和颜悦色,“你去,美琳是客人,怎么让她找?”
“美琳,快过来!”吴太太说。
“我看不见!”美琳踢踢哐哐翻东西的声音。
“丹萍?”葛太太使个威胁的眼色。丹萍这下忙抄起手电跑过去。
房间这时又褪暗了。“脚背都肿了,”吴太太把目光从葛太太的月白袜子上收回来,叹道,“你这又是何必?”
“我不小心啊,”葛太太哭笑不得。
“咱们当家属的,谁不是提心吊胆?就算真遇上了,为孩子想,也要放宽心。”
“什么?”葛太太脸一紧。
“你没听见说?”
“出事了?”葛太太一仰身,腰上没力气,又摔回床上。
“你躺着,”吴太太忙按着葛太太肩膀,往外看看,两个孩子叽叽喳喳不知说什么。她凑到葛太太耳旁,“说是淹死一个干部。”
“怎么能?”葛太太一激灵。
“嘘,别让孩子听见,”吴太太压着嗓子,“风最大那回,你忘了前两天码头上都吹跑辆吉普?就那晚,海上起大浪,一个浪头没准,把个人直接从甲板掀海里去了……”
“哪个舰?”葛太太下死眼盯着吴太太,一手不自觉狠狠扣上了她的细胳膊。
“就是不知道哇,”吴太太弓着身子,奋力把胳膊抽回去,“你听我说,这个人还没事,刚掉下去,几个胆大的就跟着跳下去了,救上来,”吴太太一拍手,“救人的一个倒没回来!”
葛太太猛地坐起来,“老葛他可不会水啊!”
吴太太忙说,“就说是个干部,不知道是谁呢。”
“他人傻实在,遇上这事,一准是他!往年还隔三差五捎话儿报个平安,怪道今年没响动,”葛太太一仰头,撞得墙咚一声,堕下两行泪来,“扔了我们娘儿俩可咋办,该怎么活?”
吴太太见状,急道,“看你这点韬量,我真多嘴!”
“怎么能让干部下去救人呢?”葛太太仰头道,“好歹也是官啊!”
吴太太抿抿嘴,不言语了。
“平实地里摔这一下子,”葛太太哭道,“不是什么好兆头……”
“阿姨,我有个事告诉你!”美琳老远喊着,推门进来,愣住了。丹萍也追着进来,跑到床前,方才刹住脚,“妈妈,怎么了?”
“阿姨摔疼了,”吴太太指着葛太太的脚踝,“快安慰安慰她。”
“阿姨,别哭,待会儿就好了,”美琳依偎到葛太太身上。丹萍站在一边,只把个暖水袋往前送。
葛太太闭着眼抹一把泪,吸口气,鼻子发出囔囔的声响,“没灌水啊?”
美琳又要去,吴太太抢道,“烫着怎么办?”
“不用了,”葛太太慢慢躺回去。
“我回家找酒精给你搓搓脚吧,很管用。”吴太太道。
葛太太在枕上微微点头,吴太太拿上手电转身走了。
“阿姨,”美琳打破沉寂,“葛丹萍还没写完作业!”
“没电……”丹萍辩白。
“你还叫我明天不记你名字!”
“我,我什么时候说唻?”
“就刚才!”美琳道,“你还让我不要说转笔器……”
“你争口气吧,”葛太太虚弱地一张嘴,又止不住掉泪,压抑得胸口吱呀作响,“生了你,妈妈可犯了罪了!”
“什么犯罪!”丹萍忙捂住葛太太的嘴,看着她的泪淌下来。
吴太太风尘仆仆地赶回来,劝道,“快别这样,孩子们都看着!”
葛太太噤了声,一歪脖子躲开丹萍的手。丹萍的掌心黏糊糊地,仿佛还有个潮湿的嘴唇贴在上面。
吴太太带来个透明塑料瓶,咕嘟咕嘟倒出些液体在茶杯里,划根火柴点燃了它,小火炉一样烧起来。她剥下葛太太的袜子,把手伸到火里迅速一蘸,拍到她脚踝上。
两个孩子看呆了。
“阿姨,你手不疼吗?”丹萍问。
“不疼。”
“这招倒新奇,”葛太太疼得龇牙。
“跟我父亲学的,”吴太太道,“烫就忍忍。”
“我外公是老中医。”美琳朝向丹萍,“你外公呢?”
“我外公,”丹萍想了想,“我姥爷家有一片枣树林。”
“就是农民嘛,”
“不,他种枣,”
“就是农民嘛!”美琳道,“你外公不如我外公。”
“你才不如我外公!”
“你学习还不如我好,”美琳得意洋洋。
丹萍气得哆嗦,直喊到美琳脸上去,“你爸不如我爸!我爸是干部,你爸是士兵!”
吴太太这时收了手,“美琳,要礼貌。”
“你偷东西!”美琳鼓起腮帮,“阿姨,葛丹萍是小偷!”
葛太太的神色在暗光里昏黄成一片,看不真切,吴太太只低头把个盖子捂在茶杯上,再掀开看看,火熄了。空气里悬浮着酒香,大家好像什么也没听见。也许真没听见,风那么大,天那么黑。
顶灯这时闪了几闪,毫不客气地亮起来。来电了,世界找回了确定性。吴太太带着美琳回家去,房门清脆地关上。
丹萍这时爬上床,把脸埋在葛太太胸前。葛太太一语不发,半晌,长长地出一口气。丹萍随着母亲的胸腔沉下去,又浮上来。
“妈妈,”
“嗯?”
“他们说,我穿那个毛衣像红毛丹。”
“谁说唻?”
“他们。”
“等爸爸回来,给你买新毛衣,好不好?”
丹萍窝在葛太太身边点点头,听见外头的风吹着。不久她就沉沉地睡去,什么也没有梦到。
皮肤白癜风能治的好吗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安全| |